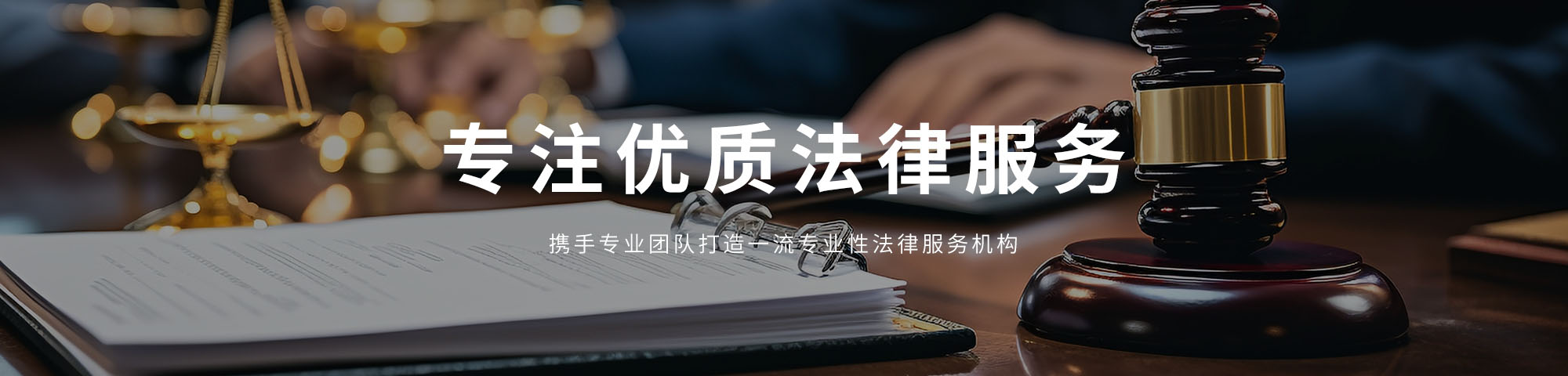


来源:东方头条 时间:2019-09-15 13:17:24
前言:一个人的生命,究竟能够焕发出怎样的能量?

董学书向进修学习人员进行蚊虫知识讲解。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供图
作为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83岁的董学书依然在蚊虫生态分类岗位上孜孜不倦,每年在最偏远、最荒凉、最艰苦的地方穿梭。60多年来,他的行程已经超过30万公里。从海拔74米的低谷到3800的高山之间,云岭大地留下他追蚊防疟的身影。

年轻时候的董学书进行蚊虫鉴定。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供图
建起国内最大的蚊虫资源库
蚊子曾是人类最大的健康敌手之一。目前,全世界已发现535种虫媒病毒,可通过蚊虫携带和传播的有近300种,近100种可以引起人、畜疾病。曾被视为“生命收割机”的疟疾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的云南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曾发生过三次疟疾大流行,滇南重镇思茅因疟疾暴发流行,人人谈疟色变,“要下思茅坝,先把老婆嫁”。1949年,思茅城区人口从3万多人锐减至1000余人,到处是“千村霹雳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
“把蚊子生态习性研究透,是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治的重要前提。”这是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蚊虫分类和生态研究专家董学书的“防蚊观”。
“即便我们都不在了,但后来人不管发现什么疾病,只要确定什么蚊子是传染媒介,翻开这本书,便可以对它的习性、生长环境了如指掌,对症防治,不就很快能把疾病消除了吗?”这是董学书的“防蚊梦”。

年逾八旬的董学书在进行蚊虫分类鉴定。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供图
这个梦一追就是60多年。
60多年来,董学书带领团队盘点云南的蚊子“家底”,收集了上万套标本,储存有云南现有蚊类标本305种。其中有新种26种,中国新纪录25种,并建起了国内最大的蚊虫资源库,累计编著了410万字的学术专著,全面总结了自1935年以来80多年间云南开展蚊类研究的成果。
2017年6月,《云南蚊类志》上下卷问世。这部214万字的鸿篇巨著,书中的384个图版、2000多幅插图,都是董学书一笔一笔亲手绘制的。
其实,董学书已办理退休手续20多年,却又退休不离岗,始终如一的坚守在蚊虫分类、生态研究和人才培养岗位上,成了“不伦不类”的,不计较报酬、不分上下班时间的“上班族”。
“生命不息,耕耘不止,将继续为蚊类分类、生态研究奋斗终生。”董学书如此表示。

现场捞幼虫。省寄生虫病防治所供图
退休后盘点“蚊子家底”
上世纪50年代,董学书从贵阳医学院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第一代疟疾防治工作者,师从第一位提出微小按蚊是云南疟疾传播元凶的后晋修教授。
在后晋修身边耳闻目染,董学书从一个富家子弟成为一名医学工作者。之后,他回到故乡思茅,把“为家乡人治好病”作为追求,开始带领群众从灭蚊开始防病……
70年过去了,疟疾这个横行云南近百年的妖魔,终于离人们越来越远了。
但梦想之火依然在董学书的胸膛里熊熊燃烧。
1996年2月,董学书退休了。
他的学生周红宁至今依然记得,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宣布董学书退休的第二天,一大早,当自己推开实验室门,一眼就看到老师已早早坐在解剖镜旁准备做“蚊虫的事”——解剖蚊虫、鉴定蚊虫、记载蚊虫、绘制蚊虫、查阅文献……
20多年过去了,天天如此……董学书一直坚守在实验室。退休后,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向董学书提出要给他发返聘工资,都被其婉言谢绝。对此,董学书说:“我退休工资够用,不需要那么多钱。”
董学书早就瞄准了自己退休后的研究方向──所里由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90年代,10余年间对全省12个地州市56个县进行不同地区、不同海拔、不同纬度,调查采集的几十万号蚊类标本,却从来没有人进行过彻底盘点。他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盘点“蚊子家底”。
在60多年的工作中,董学书越来越意识到,研究蚊子、保存种质资源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于卫生防疫事业发展、保障人民健康意义非凡。
蚊子,在平常人看来一个模子般样。可在董学书心中,各种蚊子品种的特征在他心里如行云流水般清晰流畅……讲起每一种,就如同打开一幅栩栩如生的昆虫图展。这些鲜活生动的影像,为他开启了发现新蚊种的艰难历程,也是董学书完成蚊子分类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研究做出重大贡献
年龄的增长,更让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于是,董学书给自己安排出一份日程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正常上下班,全年365天,都是工作日。事实上,除了生病,他都心乐着“斗蚊”之事。
在董学书的儿子看来,家,只是父亲吃饭、睡觉和休息的地方。“实验室更像是他‘家’。他在实验室里的时间比在家还要多,平常要找他,也只能在实验室才能找到。即便回到家后,他经常说到的一句话‘某个实验做完了,可以写论文了’,或者说‘某幅图还没绘完,还要去加班绘图去’。”
苦心人,天不负。
退休20年来,董学书用“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个“第一”:他出版了《云南蚊类志》上下卷、《云南按蚊检索图》《中国按蚊分类检索》《中国媒介蚊种图谱及其分类》《中国覆蚊属》等书籍。这些专著已成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生态研究的教科书,为中国蚊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数据。
他还参编了《中国蚊类志》《云南疟疾》等书;在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蚊虫学术论文108篇;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6项云南省政府科技成果(进步)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5项省部级、省级科技成果(进步)奖。
他还发现蚊虫新种26种,中国新纪录25种,媒介蚊种4属、24种……同时,在国内外首推雌蚊尾器分类研究,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研究和蚊媒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还无私地把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后辈,培养了数百名国内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其中许多学生如今已成为各国蚊媒传染病防治研究骨干和中坚力量,对中国“一带一路”卫生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即便这样,在董学书的“蚊子梦”里,还有许多空缺。他曾感慨地表示,如果老天能再给他20年,他要编著完成中国周边国家的蚊虫志,为东南亚虫媒传染病的防治研究提供有效防控对策奠定基础。
不过,回忆60余年的蚊虫生涯,董学书也感慨,自己没有辜负老师以及家乡父老的期望,生命因此而闪闪发光。
云南网记者 彭锡